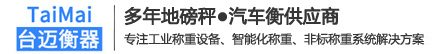王建军半个身子探在一辆翻开引擎盖的国产车里,额头上的汗珠子汇成小溪,沿着鼻梁滑下来,滴落在那滚烫的发动机护板上,滋啦一声,蒸发成一缕白烟。
他靠在冰凉的东西车上,掏出那只屏幕现已有些划痕的手机,娴熟地址开了一个二手车的应用程序。
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,掠过那些了解的、平凡的家用车,终究,停在了一则法拍信息上。
他似乎能隔着屏幕,闻到那真皮座椅在年月里沉积下来的、混合着木饰与尘土的共同气味。
晚饭的桌上,三菜一汤,热气氤氲。赵秀莲正往儿子碗里夹着一块排骨,嘴里想念着下学期补习班的费用又涨了。王建军扒拉着碗里的米饭,眼睛却没个焦点。
赵秀莲夹菜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。她渐渐抬起头,看着老公那张被油污和日子磨炼得有些粗糙的脸,目光像淬了冰。“王建军,你该不会是修车修糊涂了?”
她的声响不大,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,砸在王建军心上。“八万块,那是咱们预备年末把近邻那间铺子也盘下来,扩展店面的钱。你拿去买个车?仍是个法拍的爹?”
“房贷下个月要还,儿子补习班的钱,我爸妈那儿的高血压药,哪相同不要钱?你买个宾利回来,它能下崽仍是能生钱?”
他仅仅觉得心里堵得慌,那个愿望,那个对尖端机械工艺的神往,像一团被浇了冷水的火,非但没灭,反而冒出了更呛人的浓烟。
他没再跟妻子争论。过了两天,他瞒着她,从自己那张存了几千块私房钱的卡里,取了钱,交了拍卖的保证金。
他对自己说,就去看一眼,就当是圆个梦。如果,如果捡个漏呢?凭自己的手工,总不至于亏。
拍卖那天,天阴沉沉的。法拍车的停车场里,林林总总的车子静静地停着,像一群被主人遗弃的动物。
那辆宾利停在最旮旯,车身上蒙着一层薄灰,几道不深不浅的划痕破坏了漆面的完好。王建军围着它转了好几圈,手指轻轻拂过那冰凉的车身。

王建军坐在后排,手心一直在冒汗。当拍卖师喊出那辆宾利欧陆的编号时,他的心一会儿提到了嗓子眼。
价格从八万开端,不紧不慢地往上跳。每一次加价,都像锤子敲在他的神经上。一个穿着花衬衫的胖子和他杠上了,两人你来我往,价格很快就逼近了九万。
王建军的脑子一片空白,他简直是凭着天性,在胖子犹疑的那个瞬间,再次举起了自己的号牌。
“八万!终究一次!成交!”拍卖师的木槌落下,声响不大,却在王建军的耳朵里炸开。
周围的街坊都探出面来看热烈,那辆尽管蒙尘但仍旧气场强壮的豪车,和这个凌乱的、充溢油污气味的小修补厂显得方枘圆凿。
赵秀莲闻讯赶来,她没有哭,也没有骂。她仅仅站在修补厂的门口,静静地看着那辆车,再看看自己的老公。
她的目光很冷,像冬日里的湖水。终究,她什么也没说,回身就走,铁门被她拉得哐当一响,隔绝了两个国际。
王建军心头一沉,但随即又被一股莫名的振奋所替代。这是他的车了。他刻不容缓地想要把它开上举升机,好好看看它的底盘,它的悬挂,它的每一个细节。
他想知道这辆车的详细分量,以便后续的整备作业。他记得很清楚,这款车的官方整备质量是两吨出面。
地磅上的赤色数字跳动了几下,终究安稳了下来。王建军凑曩昔一看,整个人都愣住了。
数字显现,这辆车的分量,比官方数据足足多出了将近四十公斤。也便是老百姓口中常说的,八十斤。
王建军的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。他把车里一切的杂物,包含备胎和东西包都拿了出来,又称了一次。
他想不通,只好打电话把他师父,现已退休多年的老马请了过来。老马六十多岁,头发斑白,但一双手仍旧安稳有力。
“建军,这分量不对头。”老马的表情很严厉,“不像是原厂的东西。倒像是有人在车上,特意加了什么‘配重’。”
车门夹层,底盘的空腔,发动机舱,一切能藏东西的当地都看遍了,一无所得。那多出来的八十斤,像一个沉重的疑团,压在了王建军的心上。
他和赵秀莲的暗斗在继续,家里成了一个只用来睡觉的当地,夫妻俩一天也说不上三句话。赵秀莲把他的换洗衣物放在门口,他默默地拿走,再把脏衣服放在同一个当地。
宾利的缺点比他幻想的要多得多。毕竟是十年的老车,电子体系渐渐的呈现各种匪夷所思的毛病。
外表盘上的毛病灯像圣诞树相同轮番闪耀,一个不起眼的空气流量传感器,原厂件就要好几千。
王建军舍不得花那个钱,他把自己关在小小的工作室里,没日没夜地研讨那比天书还难明的英文电路图。
越是难啃的骨头,他越是要啃下来。可那个关于八十斤的疑团,一直像一根刺,扎在他的脑子里。
他把车里的内饰板一块一块地拆下来,座椅也整个搬了出来,车里空荡荡的,只剩下一个金属的空壳。
他一次又一次地称重,那多出来的分量仍然固执地存在着。经过重复的丈量和核算,他终究确认,多出来的分量,重心就在车身的后半部分。
王建指关节用力敲了敲,传来的声响却让他心里一动。那声响太烦闷了,完全不是单层钢板应有的那种洪亮的回响。
他又喊来了老马。老马拿着一个强光手电,简直是趴在后备箱里,一寸一寸地查看。

总算,在一个极端荫蔽的旮旯,在地毯压条的下面,他发现了一丝纤细的、不属于原厂工艺的焊接痕迹。那条焊缝处理得十分高超,若不是故意寻觅,底子看不出来。
“建军,这儿被人动过。”老马站动身,口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发觉的严重。“这后备箱的地板,怕不是个夹层。”
他买下的,到底是一辆什么样的车?原车主为何需求费这么大的劲,在后备箱里做一个夹层?私运??仍是其他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?
一个可怕的想法在他脑海里闪过。他想起这辆车是法拍车,原车主是涉案被查封的。他忽然觉得这辆宾利像一个棘手的山芋。
他面对一个挑选。是把车从头装好,修好那些电子毛病,然后尽快把它卖掉,伪装什么都不知道。
这双手天然生成便是用来拆解和探求隐秘的。巨大的好奇心和作为一个匠人的执念,终究战胜了心里的惊骇。
老马看了他一眼,没说话,仅仅默默地址了允许,回身去东西柜里,拿出了一台角磨机。
夜现已很深了。修补厂外面的国际安静了下来,只要几声悠远的犬吠。厂里,那盏老旧的日光灯把一切都照得惨白。王建军戴上护目镜,手里握着沉重的角磨机。
赵秀莲不了解什么时候来了。她没有进车间,就搬了个小马扎,坐在修补厂的大门口,也不说话,仅仅静静地看着里边繁忙的老公。
火花四溅,像一场小型的焰火,照亮了王建军专心而严重的脸。他小心谨慎地,沿着那道简直看不见的焊缝,一点一点地切割着。金属的焦糊味充满在空气里。
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绵长。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和角磨机的轰动形成了共振。老马站在一旁,手里拿着一根撬棍,神态比王建军还要凝重。
总算,跟着终究一点衔接被堵截,王建军关掉了角磨机。他用撬棍缝隙,和老马一同,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
钢板的下面,并不是料想中的车体大梁,而是一个黑洞洞的、被精心伪装过的暗格。
他现已没有耐性去找钥匙了,他从东西箱里拿出一把大号的一字螺丝刀和一把锤子,对准锁芯,狠狠地砸了下去。
他深吸一口气,手指抠住金属盖子的边际,伴跟着一阵令人牙酸的金属冲突声,将盖子渐渐摆开。
就在看清里边东西的一会儿,王建军像是被看不见的东西狠狠捶了一下胸口,整个人如遭雷击,大脑一片空白。
他手中的手电筒“啪嗒”一声掉在地上,光束在油腻的水泥地上张狂地跳动了几下,终究指向一个旮旯。
他双腿一软,踉跄着向后退了两步,一跌坐在冰凉的地面上,双眼圆睁,嘴巴微张,完全傻眼了。